人物简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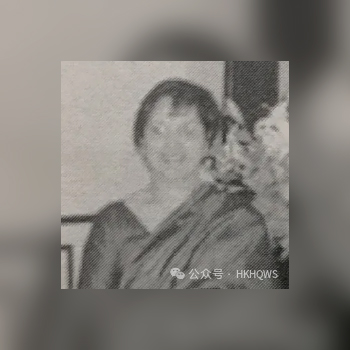
莫希妮·梅农印度前驻华大使夫人 。
通过“胃口”介绍印度文化
作为校长,莫希妮·梅农夫人在北京的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印度使馆小学里度过的。当然,这不妨碍她偶尔参加其他有趣的社会活动,比如慈善义卖。

印度驻华大使夫人莫希妮在官邸。(图源:《驻华大使夫人们》)
夫人对我讲起了最近一次义卖活动:
我非常支持这次活动,同时这件事也不是我个人的功劳,整个使馆的同事们都为此做了很大贡献。当义卖主办者和我们取得联系,问我们是否愿意为这个活动做些什么时,我们当然乐意帮忙,虽然当时使馆里很忙。
于是我们开始负责各自的展台。关于义卖的食品,大家一起出主意,然后每个人都自愿贡献出一道菜。当时天很热,我们得确保食物不变质,所以义卖那天早上我们才开始做饭。我自己要做两道菜:咖喱饺给素食者,咖喱鸡肉米饭给非素食者,而且米饭里还掺了红豆,都是很好吃的东西。
义卖活动当天,我自己主要是销售印度茶叶。那是一种很有名的印度产品。上次我们卖的是印度的小饰品,明年还可能卖别的东西,每年都会不一样。同时在现场还有一位印度女士给人看手相,完全是为了增加乐趣,却吸引了很多人,结果她的表演好像比我们卖的食物还受欢迎。
相对于上次活动,这次让我更感到高兴,因为有很多中国人来参加了。这不仅仅是慈善活动,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通过它向中国人介绍我们国家的文化。
我想,通过‘胃’来介绍印度的文化是个好主意,因为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行得通的。正是通过这次活动,我得到了一个让中国人品尝真正的印度食物,特别是真正的印度咖喱的机会。
母女两代人和同一所印度小学
莫希妮·梅农夫人的印度使馆小学是她在北京生活的快乐源泉。
印度小学始建于1967年,创建人是时任印度使馆代理大使的妻子沙莉,而她正是莫希妮·梅农夫人的母亲。当时印度使馆里一共有35个孩子,而北京还没有一所英语学校,孩子们因此都无法上学。
我母亲和使馆里其他外交官的夫人说,‘为什么我们不为孩子们开设一所自己的学校?’于是她们开始行动了,筹划的事情由我母亲一手操办。起初只是为了印度使馆的孩子能上学,结果后来有很多外面的孩子也来了。
刚开学,学校没有教室,我母亲说,‘我们可以用一部分屋子来做教室’,所以现在的小学所用的教室实际上是大使官邸的一部分,教室的后面就是大使的住宅。
这所学校至今(2002年)已有35年历史了,它由历届的大使夫人来掌管。现在,我成了学校的校长,既有管理的职责又有教学的任务,因为我既是校长也兼教师。
我的学校里有不到200个学生。他们来自32个不同的国家,大部分都是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。
孩子们到我的学校来有几个原因:这所学校是初级学校,学生们都是4岁到10岁的孩子,我们实行半日制教学,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1点,无论是时间还是课程的安排,对这么小的孩子都是非常合适的;学校地点对很多住在使馆区的孩子来说很方便,因为外面的学校都在离北京市区很远的地方。
还有一个原因是学费,我不需要做广告,因为我们的学费很便宜。每年一到开学的时候,学校里的学生就很满了。我的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几年,然后他们会到其他学校去继续上学。我们用英语教学,主要沿用印度的教育体系管理。这不是使馆区唯一的小学,但却是唯一一所专门由外交官夫人主管的学校。
梅农夫人对此颇为自豪。
选择教书是因为喜欢求知
采访那天正赶上阴雨天,庭院的草地上,秋千、滑梯、单杠等孩子们爱玩的东西都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。课间休息时,不能到外面活动的孩子们只好待在屋里,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活力。
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五六岁或再大一点儿的孩子聚在楼道里,活泼地尖叫着做各种游戏。莫希妮·梅农夫人则站在外面的门廊里和老师们说话,不时提醒着某个淘气的孩子小心别磕碰着。
以前的大使夫人都只是掌管这所学校,她们不教课,但我喜欢教书。我教英文,对我的学生在功课方面我很严厉,如果他们不做作业我会生气。
我们有专门的中国老师教音乐和中文,中文在学校里是第二种语言。我们还对部分课程适当进行了调整,比如增加了教太极拳的课程。我很幸运有这样一支有良好资质而且工作勤奋的教师队伍,在每年一次的运动会、戏剧节等活动中,他们都有着良好的集体合作精神。
在我和夫人伴着钢琴声聊天的时候,孩子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排练,一队小孩子甚至把队伍排到了夫人的办公室。夫人站起身,打开电脑,里面还保存着2002年举行的音乐会照片,那上面的孩子们都穿着印度传统服装,在表演印度舞。

莫希妮和印度使馆小学的教师们合影。(图源:《驻华大使夫人们》)
就在几天前,印度使馆还刚刚组织了一次绘画竞赛。这个活动每年举办一次,参加者主要是印度小学的学生,同时还邀请一些中国的学生参加,获奖作品将被送到印度展出。莫希妮·梅农夫人对学生们的绘画作品感到非常震惊,她说简直太好了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用宣纸画画的中国学生的作品,后来他被邀请来使馆,为夫人画了幅荷花。
莫希妮·梅农夫人和教育工作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大学刚毕业时,她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驻印度机构做编辑。但当她开始伴随丈夫到其他国家时,她就不做编辑而改为授课了,“因为在各个国家你都能教课”。
在过去的17年里,她随丈夫到过五六个国家,她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教过英语,其中包括前后三次来中国。这期间,她也曾回到印度,当过几年教师,在一家非政府的慈善组织里给患有痉挛性疾病的孩子们上课。
我当时有机会教正常的孩子,但我更愿意教这样的孩子,是因为教这些学生需要更大的耐心,同时我也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回报。
“你看!”夫人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让我看,上面写道:
我当教师是因为我热爱学习。只要我教书,我就要不断学习。在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:我教得最好的不是我已掌握的知识,而是我想学会的知识。
夫人说:
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,但却是我的哲学,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教书的原因。
教育就是种下思想
莫希妮·梅农夫人2003年新种的小树苗和各种已经发芽的植物正在花园里茁壮生长。夫人告诉我说:
我对园艺种植十分感兴趣。事实上,在使馆里,每年都要更新花园,因此我们种了很多中国的树。通过养花种草,我了解了很多中国植物。虽然一些苗木能长大,而有些植物到了秋天就会死掉,但这不要紧,我从种植它们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乐趣。
梅农夫人说自己很幸运,因为当她住在不同的国家时,她可以学习各种不同的培育花卉的方法。当然,作为经常辗转于各国之间的外交官夫人,她唯一的遗憾是不能总是看到自已精心种植的植物长大。
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,园艺设计的理念也有所不同。我读了很多关于园艺方面的书,到不同的地方可以学习不同的园林理念。
有件事情我觉得很神奇,在中国,人们特别喜欢用花盆来栽种植物,而在我们那边,则更愿意直接把花种在花园里。比如说荷花吧,在印度或斯里兰卡,就我所知,人们从不用盆来栽种,因为荷花从来都是长在湖里或者是河里的。到中国以后,我曾拍了很多养在盆里的荷花照片。回到印度我把照片送给我的朋友们,他们都非常惊奇,不能相信盆里也能种出荷花。我想,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气候不同。北京的冬天实在是太长了,雪也多,培育荷花的方法和印度当然不一样。
我至今还没参加过中国的园艺活动,但我很想参加。所以,我在旅游的时候,更愿意去有园林的地方。苏州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,特别是春天去那里简直好极了。
问到种树养花和教书育人有什么联系,夫人笑道:
这两者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,大概都需要耐心,都有很多的乐趣。教育孩子就好像在他们的头脑里种下思想。
父母的期望不等于孩子自己的希望
莫希妮·梅农夫人和丈夫分别出生于两个世交家庭里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,后来又都上的是新德里大学。莫希妮·梅农夫人学习英语,丈夫比她高一个年级,学的是历史。
上中学和大学期间,夫人学过印度的古典舞蹈。她很喜欢这门课程,还自己找了个老师,专门学习印度舞,从中深化自己对印度文化的了解。夫人甚至对我很怀念地讲道,从她结婚并离开印度后,就再没机会继续学习印度舞蹈了,实际上她已放弃跳舞很多年了。
莫希妮·梅农夫人的父亲也曾于1979年任过印度驻华大使。她说:
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,我从妈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她曾在大学里学过医学,虽然结婚后就放弃了学业,但她是一位有很多兴趣爱好的家庭妇女。
与50多年前相比,现在的印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妇女结婚就放弃工作的现象已不很普遍了。我父亲是外交官,他到过十几个国家。在我10岁以前,我一直都跟着他们。
10岁以后,我被送回印度,上的是寄宿学校,因为我小时候国际学校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。那时候,我每年两次去国外看望我的父母,我从中知道了自己非常非常热爱旅行,而且通过旅行,我变得眼界开阔,变得更喜欢去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。能够在世界各地旅行,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大优势,我很幸运能有这样的机会。
作为印度驻华大使夫人,莫希妮·梅农如今很希望中国人了解印度的文化和悠久历史。
我会通过各种途径向外国朋友介绍印度,希望他们能通过我的眼睛去了解它。印度人都很热情好客,却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个个能歌善舞,但我们都喜欢音乐。我认为印中两国在文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,比如我们都注重家庭。
在印度,妈妈们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。说到自己的一双儿女,我一直认为我是个严厉的母亲,因为我总是让他们做这做那。我从小就鼓励他们要独立,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,即使他们有时会犯错误。
如果孩子不吃饭,从饭桌旁淘气地跑开了,别的母亲可能要追着他们喂饭,但我不会,我总是对他们说,‘你们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吃饭,你们自己吃,过时不候。’
即使他们不小心将饭粒弄得到处都是,也没关系。他们慢慢就知道了如果不吃,到时候饿了,妈妈就不让他们吃饭了。
我还让他们自己写家庭作业,我从不帮忙,除非他们有不懂的我才讲。
孩子们小的时候,我总是让他们晚上7点半准时上床睡觉,到了10岁就是8点睡觉,但有意思的是,孩子们从不记得我的严厉。当他们长大后我问他们,‘我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吗?’孩子们都说,‘不,我们不记得你是个严厉的母亲。’
我的两个孩子童年时跟随我们到过很多国家,不像我小时候那样得住寄宿学校,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有很多国际学校。再说,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分离。我小时候,父母是没有办法才送我走的。我希望我的孩子尽可能多些时间待在我身边,直到他们上大学。现在他们长大了,他们告诉我自己曾有一个非常美好、有趣的童年。
我的女儿现在27岁,已经结婚,正在美国读博士学位,博士论文做的是心理学与印度电影。我儿子今年24岁,大学毕业时拿到了数学和中文两个学位,现在在美国读数学博士学位。
我不知道孩子们今天的成就和小时候我对他们的教育有多大关系,但我想这与我和丈夫经常教育他们从小就要热爱学习是有关系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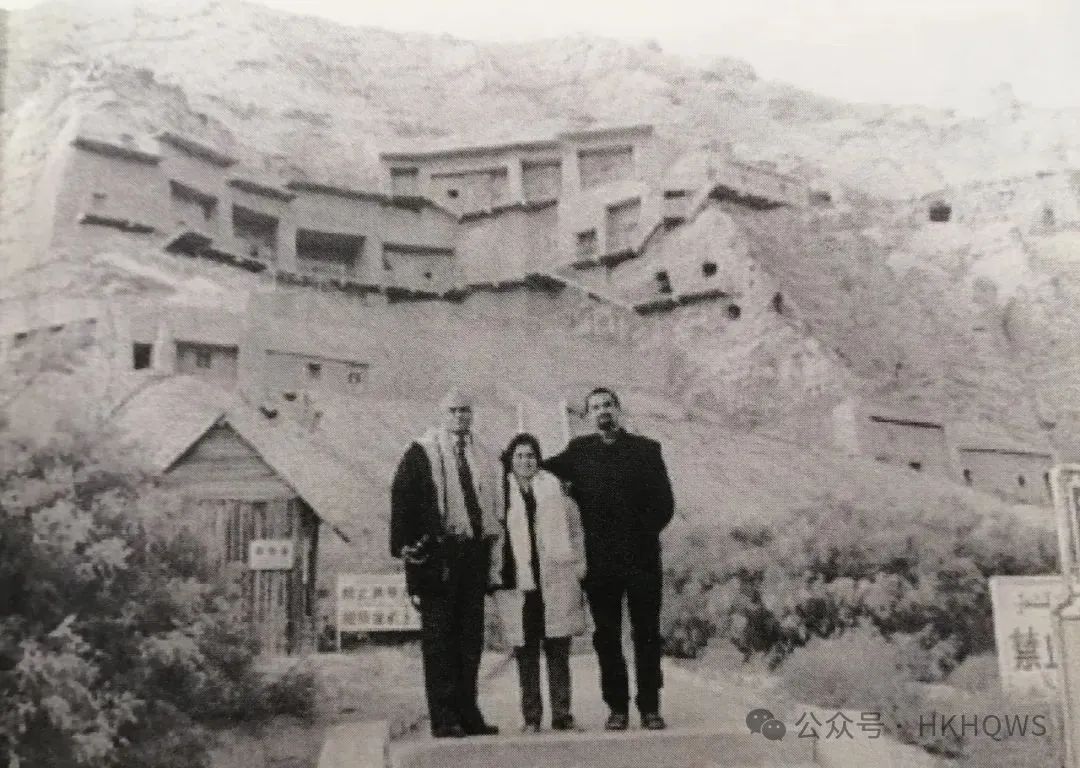
大使夫妇和儿子在新疆观光。(图源:《驻华大使夫人们》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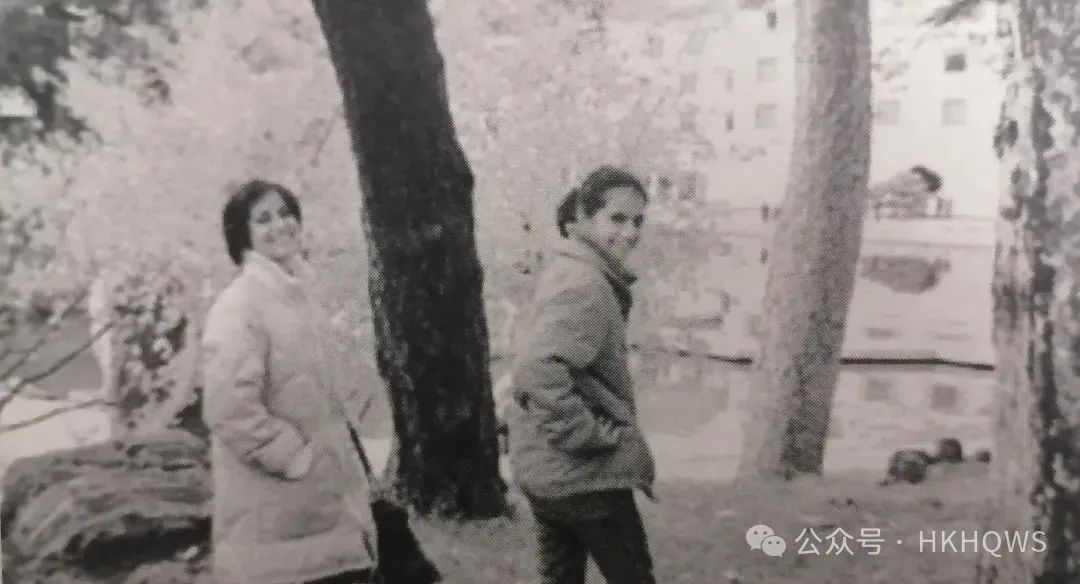
莫希妮和女儿在北京香山。(图源:《驻华大使夫人们》)
至于一双儿女的将来,夫人笑说那是他们自己的未来。
无论他们想做什么,我都会支持,我不会为他们去设想。现在,他们都达到了我的期望,但我的期望并不等于是他们自己的期望,我仍旧鼓励他们自己做出选择。
图文转自: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
